异化的大学教育:一点个案观察
这篇题为《大学教育观察》的文章是作者在高校任教近一年后的深度反思,文字诚恳,情绪浓烈,论述绵密。整篇文章的主旨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在大学教育中,教师和制度是否真正关注学生的成长与需要,还是已经沦为追逐KPI和行使权威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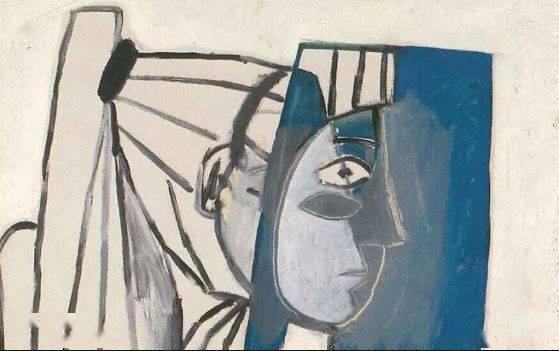
前言
当大学老师快一年了。我对教学有原始的热情。我秉持这样一种理念:教育的目标之一是开拓视野,激发兴趣。具体而言就是,让学生了解这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些问题,事情还可以这么思考,由此激发学生探索未知的兴趣。部分原因也在于,我知道我所能掌握的东西,对于所讨论的问题都是极其片面乃至错误的,我最多向他们展示我所拥有的思考,这些思考绝不是像课堂上展现的那样确定、全面乃或正确。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这样的视野开拓,学生可能就没机会了解,更不用说爱上什么东西。有时候我们说自己不爱一个东西,可能仅仅是因为还不了解这个东西。教师的使命之一在于向学生揭开某个世界的一角面纱。至于学生会不会最后感兴趣,则是要看学生的性情偏好。在这篇文章中,我选取了几个要点,简单谈谈我的一点个别化、不完全观察。
教师的 KPI,学生的灾难
此学校是一个教学型而非教学科研型学校。不卷科研卷教学,但卷教学可能更难受。课堂教学仅仅是“教学”的一个子项,指导学生参加各种竞赛也算教学的一部分,而且是职称晋升必要的项目。我正赶上学校对三年前入职的教师的阶段性考核。讲师至少每学年 170 学时的教学量(评副教授还需要至少 240 学时)。这个要求在同事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按照学校的规定,老师每学期开课不超过 3 门,大多数课程的课时在 34 学时左右。这意味着每位老师至少每个学年要开 5 门左右的课。这看起来也不算太多。不过对于有的专业的老师而言,他们的课本来就少,经常是一个学期就开 1 门课。
这种考核的出发点是什么?第一,学校的总课程量足够所有老师开设的;第二,老师可能因为不想开课而使学校无法完成教学计划。我不清楚学校是否弄清这两个出发点。根据我的观察,许多老师开课热情高涨,一年能上三四百学时。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允许部分老师少上一些课呢?
这样的考核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原先上课少的老师积极寻求开课。之前不开的选修课也开起来了。之前给其他老师机会的必修课,现在也要拿回来。由于这种考核,总的开课量可能会有一定比例的提升。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所有人只关心自己的 KPI,而没有人关心学生的需要。学生真的需要那么多课吗?大多数照本宣科的课对学生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良心问题。本来,上课的出发点是教育,而教育的出发点是学生的需要。但在制度设计和执行的过程中,学生的需要似乎是最不重要的事情。
对此,有必要提几个关于大学课堂教学的事实:
大学的一部分课程是帮助学生打牢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一般设计为必修课程)。
另一部分课程是帮助学生开拓视野、激发兴趣、了解方法的(一般设计为选修课程)。
大多数老师平庸或懒惰,其必修课所教根本超不出教材的内容。
大多数必修课的作用仅仅在于强制学生在一个固定的场合学习。这对于相当一部分没有学习动机或自律能力差的学生是必要的,但对于相反情况的学生而言是多余的。
大多数必修课根本无法起到开拓视野、激发兴趣、了解方法的作用,仅仅是为学生提供一个混取学分的机会。
总的来说,在今天这个互联网和 AI 时代,大学课堂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逼迫平庸的学生学习,主要结果是浪费优秀学生的时间,且许多课程的课堂教学并非不可替代。
所以,每一个课程制度设计者都要自问:“我们这些课程真的是学生学习这些课程的知识所必需的吗?”而每个教师个人也有自问:“我在这门课上能够提供超出教材以及互联网资源的东西吗?”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课堂教学就其实是学习知识的阻碍。课堂教学就只有一个可辩护的理由:逼迫平庸的学生学习。确实,对于许多学生而言,课堂教学是他们为了真正和自主学习而要克服的最大障碍。每一个优秀的学生都在想方设法最大化利用课外时间,而课堂教学是他们沉重的负担。
许多老师是上课狂,但开课的目的完全只是挣课时费,甚至到了完全不顾学生死活的地步。这绝不夸张,请看两个学生的课表:
这样的教学安排下,学生哪还有喘息之机?为数不多的完整时间,还要被班主任训话和各种创优活动挤占(要求学生搞这些,同样只是为了自己的 KPI。)。他们还需要休息,还需要娱乐,还需要健身,还需要社交,还需要恋爱。这样的课程密度,学生上大多数课只能即听即走。
在看到这样的课表之后,我不能奢望我必修课的学生在上课之前抽出完整的两个小时来预习,更不用说课后抽时间复习了。我对选修课的定位是:选修课就是一台戏,教师就是戏子,学生就是观众。不要指望观众来看戏之前还把你的剧本预习一遍,当然也不要指望观众看完戏之后还把你的剧本复习一遍。所以我甚至不怎么敢布置阅读材料。即使布置有限的材料,也不强求学生阅读。
万恶的题库
我来到这个学校后,发现超星这个文献阅读软件已经开发出了学习通这样的教学管理软件。这个软件的一个重大特色是极大便利了题库建设以及学生的刷题学习。异化也因此而始。过去没有这样方便的系统之前,对于教师,他没有办法把教学变成一个纯粹的测试过程,对于学生,他们也没有办法把学习变成一个纯粹的刷题过程。习题册确实早就存在,但所谓上课只是把习题发给学生反复测试是难以想象的。学生也只是在学期末时打印习题册疯狂背题,平时还是以看教材和听课为主。回想我本科学医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方式。这也还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一来本科医学几乎全是死记硬背;而本来医学对于我来说并不是本业。但对于与此同时要学习的法学来说,我从来没有使用过习题册,老师也从来没有释出这种东西。
现在的情况是,许多课程教学围绕题库进行。平时的教学并不用来研究理论问题而是用来刷题。期末考试设置了 70% 以上的客观题,主观题的分值少的可怜。一道简答题的分值只有区区 3 分,以至于让人想起了“性价比”。我从一位老师那里了解到,他们最大的一个担忧是学生普遍不及格。所以除了让学生刷题和大比例客观题,似乎没有别的办法。
我所在的学科法理学则是另一番奇观。法理学被院领导兼学科带头人建设为国家一流课程。这个课程依托学习通建设。在上面建立了上千道的习题库。每个章节都有知识点讲解视频、章节应知应会、课件、章节测试。总之,学生完全可以借助这个系统自学。课程因此也采取所谓线上线下混合模式:学生线上学习这些资料;教师上课只测试学生的自学效果。
这个课程的设计的初衷我先不谈。先说一下最终的效果。我第一学期完整听了这位领导的课。他上课首先是给学生发第一个测试, 20 道选择题,5 分钟内做完。然后花费一到两堂课来讲题。讲完之后,他会再发一个测试,是更简单的二选一判断题,用于测试学生对刚才讲题的听课情况。然后继续讲这第二个测试。如果还有时间,就会继续发第三个测试,也是 20 道 5 分钟,用于测试学生对下一章节的预计效果。下次课,继续讲上次课的第三个测试。如果上次课没有能够发第三个测试,则上来又是新的测试。
我一开始并未在意。但是,在听了半个学期甚至到了期末之后,我才惊讶地意识到,原来他一个学期 51 个课时,居然始终不断地测试和讲题。我于是想,一流课程评审专家坐下来听听他一两节课这么讲题,考虑到整个课程资料和架构的设计,倒也觉得非常好,但他们的失误就在于没有一整个学期都去听课。
怎么评价呢?首先,这是人类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案例。无论任何阶段、任何学科、任何性质的教学,它都开创了全新的案例:始终不断测试和讲题。数学竞赛班不至如此,法考培训班也未这样,何况,这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
其次,这种围绕题目进行的法理学教学与法理学完全无关,甚至说是反法理学的,是对法理学的戕害。法理学有一系列的重大主题,比如什么是法律、法律与道德关系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法律,我们为什么要服从法律,法治是什么,如何解释和适用法律,各国法律制度有什么不同,不同历史阶段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有什么不同。这些重大主题没有一个有确定的答案。它们都是充满固有争议的,而不能被切割成一个确定无疑的知识点。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了解这些主题的相关争论,为他们提供一些可用的思路,开拓他们的视野,激发他们的兴趣,培育法律思维和法治精神。学生了解这些,未必要自己也能完全明白讲出来,甚至不必有相同的观点。但是这仍然是一种教育。不是只有能够做题的教育才是教育。
再次,法理学的教学与法理学的重大主题几乎无关。出于试题导向的设计初衷,这门课大部分内容都是教义学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法律的渊源部分还其实是中国立法学导论的一部分。这些教义学对各种法律概念进行了特别细致的分类。比如把法律关系分成纵向-横向、主-从、第一性-第二性,把法律概念也分成描述性概念、评价性概念、论断性概念、描述不确定性概念、规范不确定性概念等等。把法律事件分成自然事件和社会事件等等。大部分内容都是各种分类。题目也是围绕这些概念和分类进行的。比如有题目会让学生决定“张三被殴打致重伤是自然事件还是社会事件”(答案是自然事件),有题目会问《监狱法》第七条是不是权义复合规则(然而这是大白话就能理解的问题)。
这些教义学分类有什么作用呢?当然是有些用处的。然而首先,它们不应该成为法理学的主流。第二,它们在理论和实践中几乎没有作用。部门法有自己精致的教义学,并不会以这些教义学为基础。我不知道张三被殴打致重伤是自然事件还是社会事件也能正确处理这个事情,甚至说,知道了反而徒增认知负担。我不知道法律规则的三要素还是四要素的逻辑构成,或许能更好理解法律规则的意思。第三,这些教义学分类,实际上来自相当不同整全法理学框架,要真能起到理解和指引的作用,必须在一个确定的法理学框架内提供。但是,这是目前任何教材都无法提供的。据我所知,舒国滢和雷磊还在不断增加分类,似乎这能彰显法理学的高超技艺一般。
第三,我们所以需要一些概念或分类,是因为有了它们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或运用对象,或者没有它们我们就不能理解或运用对象。概念分类不是目的本身。但是,像中国当代法理学教材中的法律规则逻辑构成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法律规则包含“可为模式”“勿为模式”“应为模式”是不是就不能理解法律条文所表达的法律规则的意思了?我不知道一个法律条文所表达的法律规则所提供的指引是不是所谓“不确定指引”就不知道它对我们提出的指引的内容了呢?最后,这些教义学概念本身充满着矛盾和问题。还是以三要素说为例。“可为模式”的一个例子是“应当排队”,但行为模式是一个事实性概念。针对一类行为(无论是已经发生的还是未来可能发生的),法律对这类行为有所要求(禁止或许可等),因而有了规范。所以任何规范,包括法律规范是对事实的处理或要求,因此,“应当排队”本身构成一个规范,其逻辑结构是“规范算子+事实”。如果“不得排队”是行为模式,那么法律规范是什么呢?法律规范是对违背“不得排队”之行为模式的回应,“应当拘留”。很好。但是说公民的行为违背一条包含三要素的法律规则的意思是什么?违背的哪一个要素?违背的是“应当排队”这部分,但没有违背“应当拘留”这部分吗?但更重要的是,“应当拘留”却不是对公民提出的要求,而是官员提出的要求。因此看来一个所谓的法律规则事实上包含了两类规则,义务性规则和制裁性规则。
问题就在于,在一些整全法律理论中,“应当排队,否则应当予以拘留”这样的法律规则实际上不是真实的一个法律规则。我们刚才提到,这些教义学概念不是对理解问题没有用,而是必须以确定的法律理论为框架。把法律体系划分为义务性规则和制裁性规则或者划分为义务性规则、制裁性规则、授权性规则,这背后依靠的是一个深厚的整全法律理论。这些并不是我们的初阶法理学教学所能处理的。没有理论,只有空洞的概念,最终我们从未在实践中使用这些概念,除了考试。
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生整个学期被上千道选择题浇灌,他们甚至都没有机会了解这些概念区分的理由和实质。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呢?这样做的结果是,学生一个学期之后根本不知道法理学是这样的一门学问。他们根本不被允许见到法理学的一角。由于学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他们反而认为法理学就是这样,这是何其悲哀?
学生仅仅被告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学生隐约感到民法需要刑法的支持,但由于根本不告诉他们法律体系的一般结构,他们永远停留于朴素的疑惑中。而提供一套关于法律体系的一般结构的理解,需要提供一套一般法理学理论基础。而提供一套一般法理学理论基础,就要涉及法理学的一系列重大的主题和讨论。而这些主题和讨论又几乎是开放的。
我的领导自豪的说,法理学由此消灭了不及格。你不能自己设定任何目标,然后让学生完成这个目标,之后说这个效果本身是在做有意义的事情。有可能,你设定的这个目标本身就与你要做的事情无关。这是法理学教育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我跟同事开玩笑说,如果我有机会决定这个学科的建设,那么我在上任的第一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删除题库。这是对法理学最重要的挽救和最诚挚的道歉。
教育的起点和归宿是爱
这个学期发生了几件小事。第一个是在答辩时,我听那个院领导亲口说他知道的几个学生的毕业论文是他自己写的。当然为的是为了成为优秀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我不明白,一个快退休的人、一个教授、一个做到了最高院领导的人,为什么还有对这样蚊子腿大小的荣誉汲汲以求?他得到的这个荣誉可能对他来说只是一滴水落入了一缸水,但对于他的这些学生的损害就像一个老鼠投进了一锅粥。通过弄虚作假来获取荣誉和利益,这种直接示范,可能对当事学生以及他们知情的同学产生持续一生的恶劣引导。
第二个是在期末期间,有班主任希望我给他的两个“得力干将”打高分。小小的举动教会了学生谋取特权。这样的学生进入社会又会是怎样的呢?这样的举动使得任何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成为学生心中默默嘲笑的对象。
第三个是一起吃饭时听同事谈起一个“问题”学生,说他上课戴耳机、喝水吃东西、不听管教。这个老前辈——向来以上课纪律严厉著称——听到之后,就立马打鸡血一般地大谈特谈如何整治这个学生。在我看来,这里的问题是,教育不应是展现权威的场合:一遇到学生有问题,马上本能地施展自己的权威,打压、嘲弄学生。教育的起点和归宿应当是爱。所谓爱,是基于学生的需要而不是自己的需要。遇到这样的学生,教师的第一反应是去了解情况,给予必要的关心,看看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遇到什么问题,以至于变成这样,而不是本能地向其施展思想拳脚。学生毕竟未成熟,他们在生活和学习上遇到许多在我们看来不成问题的问题本来就很正常。如果他们都能正确处理,那还需要教育者做什么呢?
还有一个可以思考的例子。我们这里的班主任经常会把学生集结起来训话两三个小时。有什么问题需要反复训斥两三个小时?学生的课业负担已如此沉重,整块时间本就不多。训斥是真心想解决学生的问题,还是行使自己的权威?有的班主任还会要求学生参加各种创优活动,把学生本来为数不多的自由时间弄得鸡零狗碎,而出发点大概只是为了自己的荣誉。学生碍于集体的压力,不得不参加各种创优活动。大部分的学生可能四年都没有看过一本课外书,整个四年专注于刷题和考试,一个学生告诉我他最大的烦恼是没有完整的时间阅读和思考。
另外一件小事是,一次四六级监考,一个学生竟然把去年的准考证拿来考试。和我一起的主考官看到后,本能地带着厌恶的语气对略显尴尬的学生说“真是有毛病”。我可以想象这样的老师对待学生的一般态度是怎样的:常年的教育工作已经让她形成了展现权威的本能。
人们说教师的最高准则是“行为世范”。我们这个学校,由于特殊的性质,可能有更多的人和做法是向着相反的方向走的。前些年,在学校的政治环境比较黑暗的一个时期,班干部、学生会干部、党员这些名额都是明码标价。也出现过班主任私收班费达几万元用于私人消费的,或者占用学生奖助资金的。在当时那样一种风气之下,一百门专业课、一千堂思想政治教育课,亿万次领导讲话也无法修补学生们年轻心灵所受的创伤。他们只会觉得这个世界虚伪、丑陋、不公。
结语
无论是从学校的绩效考核,还是课程的建设,或者日常的管理,我们的教育工作者都需要始终谨记的一件事是,什么是教育的起点和归宿。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但是当教育异化为追求自己的功名利禄,异化成施展自己的专横权威,那么伤害的不仅是这些学生,还可能是整个民族的心灵。
我知道,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教育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没有一点现在比过去的教育更堕落的意思,尽管我自己的观察和经验让我有所怀疑。教育风气的败坏,根源在于教育者心灵的败坏,而这又根源于整个时代精神的败坏。
我听我在乡镇上学的侄子说,他们食堂采用学期预付制,他们每次领到的鸡蛋几乎都是臭的。但是当上级来检查时,他们将吃到那学期最好的饭菜。另一件事是,他们的班主任不准他们课间休息出去,对上课去上厕所的学生极力打压。这导致我侄子三天都不会排一次便。(众所周知,如果便意来了不及时排便,就会很快消失,排便不规律又会导致便秘。)前几天我在短视频也刷到,一些学校的学生大面积便秘,原因就在于老师过于严格的管理。我还听侄子说,他们的数学老师会让他们像朗读语文课本一样对着黑板朗读数学题答案,以至于最后全班人的嗓子都哑了。
这个个案观察加深了我的忧虑。至少这在我的那个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一个班主任要多不考虑孩子的需要才会这么骄横地使用权力。一个学校要多么败坏才会将教育变成一种敛财工具?我总觉得,比起我们当年的老师,我们这代人的孩子的教师整个精神面貌变差了。到底是什么使教育工作者变成这样?教育工作者也曾是被教育者,更重要的是,教育工作者自己也处于一个他们无法改变、与之共谋的社会和时代环境之中。
